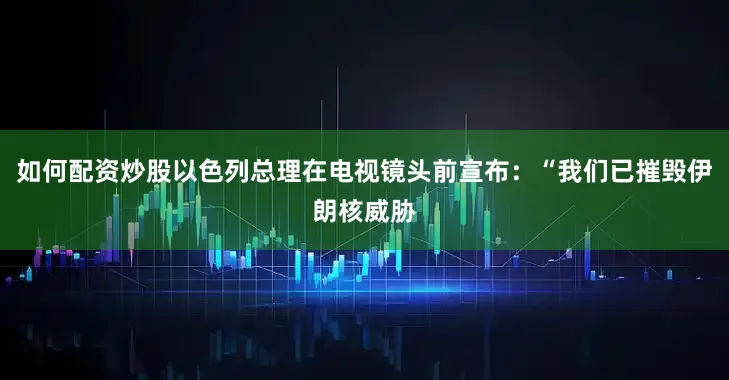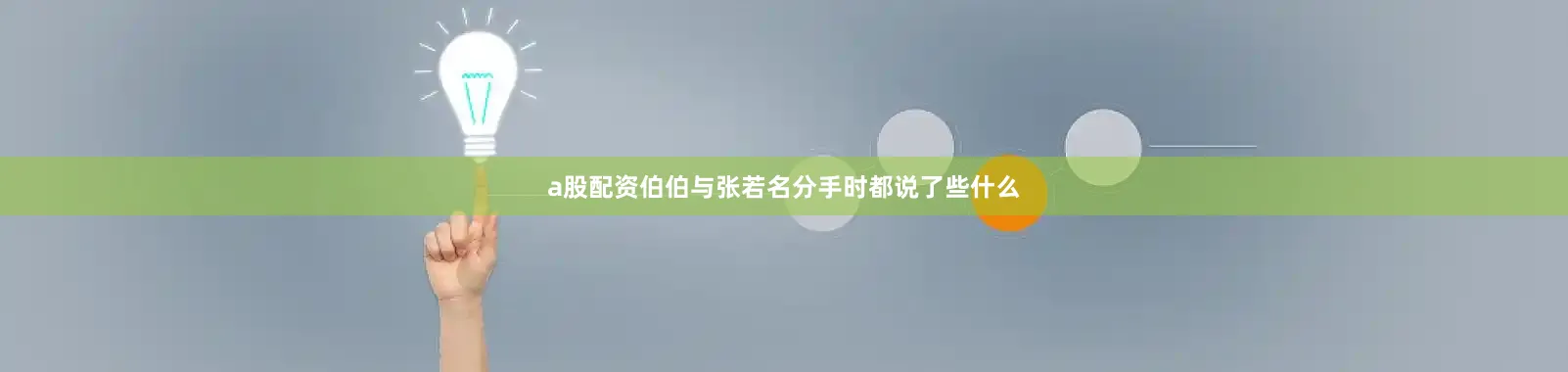
近些年来,网上传颂着不少周总理与邓大姐的书信。
其中的一些话语,被许多网友视为很浪漫的“爱情金句”。如“望你珍摄,吻你万千”“我这一生都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,唯你,我希望有来生”等等。
周邓爱情,在经过时间的洗礼后,成为一种被后来人所羡慕的模范爱情。
不过,作为一对革命者和政治家,要描述和理解他们的爱情,绝不止这些甜蜜的情话而已。
01
大约在1923年春天,远在欧洲的周恩来给邓颖超寄来一张明信片。
这张明信片上印有李卜克内西和罗莎·卢森堡的画像。他们是当时第二国际的左派领袖、大名鼎鼎的马克思主义者,也是一对革命的伙伴,在1919年被德国政府杀害。

图为李卜克内西和罗莎·卢森堡的画像。
他们两人的牺牲,似乎对周恩来的震动很大。在旅欧的几年时间里,他不止一次在给同学好友的信里,附着这两位革命者的画像。
只是,给邓颖超的明信片有所不同。周恩来在那上面还亲笔写着一句话:
希望我们两个人,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那样,一同上断头台。
这句话的意思再明确不过了。
除了周恩来,又有谁会用“断头台”来告白呢?
然而,邓颖超起初还不太敢确定,因为她知道与周恩来同去欧洲的,还有一个张若名。
张若名是邓颖超的同学,也是天津进步学生团体“觉悟社”的成员。在这个团体里,张若名是个才女,文章写得好,据说长得也比较漂亮。
而邓颖超年龄比较小,“像个虎头虎脑的假小子”。因此,社里的不少同志都没把她和周恩来联系在一起,都认为周恩来和张若名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
邓颖超也这么觉得。

图为觉悟社部分成员合影。邓颖超在前排右三,周恩来是后排右一,可惜张若名没在照片里。尽管照片很小,但也可以发现,总理青年时确实很帅。
可为什么周恩来要“舍近求远”,舍弃了张若名,选择了邓颖超呢?
经过巴黎的一段生活,周恩来看出来了,张若名不会是那个会跟他一起上断头台的人。
张若名出生在河北一个名门望族,祖父是当地的首富,父亲是一个官员。用今天的话来说,她既是一个“富二代”,也是一个“官二代”,有着优渥的生活条件。
邓颖超的出身则很不一样。她早年丧父,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几乎一无是处。她自小就跟着母亲辗转各地,在社会的底层摸爬滚打。这样的出身背景,往往更容易造就一个坚定的革命者。
虽然张若名跟周恩来一起来到法国,不过他们最终还是渐行渐远。张退出了政治,后来成为了一位优秀的学者。但她的最终结局,也令人唏嘘。
1950年代,周总理曾亲口对侄女周秉德讲述了这段往事,他说:
我的终生伴侣,理所当然必须是志同道合的。于是,我主动同张若名说清楚,转而与你七妈频繁通信。
周秉德女士在书中说,她真想知道,伯伯与张若名分手时都说了些什么。
其实,我也想知道。
02
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,有不少赫赫有名的女性,往往都隐藏在丈夫的光芒之下。也正由于丈夫的光芒太过耀眼,她们真实的形象就显得较为模糊。
譬如,孙夫人庆龄先生。她留给世人的印象,通常是梳着一丝不苟的发髻,姿态优雅,浅浅微笑。可了解她的历史,会发现庆龄先生是一位极其爱憎分明、敢做敢为的人。
邓大姐也一样。她并非全然如外貌给人的含蓄而柔软,而是一个颇为犀利且坚韧的人。
有两个故事,很可以反映她这种个性。
1925年夏天,邓颖超来到广州与周恩来结婚。那时,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,周恩来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,在家中宴请同僚。
这些同僚中,有国民党也有共产党,他们日后都赫赫有名:张治中、邓演达、何应钦、邓中夏、陈赓等。
饭吃到一半,张治中听闻邓颖超曾在五四运动中当演讲队长,就提出让她讲恋爱经过。大家一听,热烈地起哄鼓掌。周恩来有点担心,怕新婚妻子应付不来。
哪知道,邓颖超以瘦小之躯站在板凳上,毫不怯场地把两人相识到相爱的过程讲述了一遍。张治中听后连声感叹道,周夫人,名不虚传。
这时,邓颖超又毫不客气地说:
什么周夫人,我有名字,邓颖超!

周邓结婚照,1925年广州。
两年之后,这一桌子上的两党散了伙。
1927年春天,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逮捕共产党人,白色恐怖来临。对早期的共产党员来说,那是一场劫难。
对邓颖超而言,那更是一场双重劫难。当时,她正在广州的教会医院产子,周恩来已去上海,只有她年迈的母亲在身边。孩子难产,医生使用产钳用力过猛,结果婴儿头部受创没有存活。
这多少算是医疗事故吧。邓颖超极尽克制理性,没有责怪医生,反而宽慰他们:
我知道你们尽了最大努力。
她的这个态度打动了本就内疚的医生。面对军警的追捕,她将自己的真实身份道出。也许是医院也想做些弥补,他们就甘冒风险,将邓颖超安全掩护到香港。最终几经磨难,成功与周恩来汇合。
我看到这段故事,深感在如此乱世,遑论是一位女性,哪怕是意志稍微脆弱的人,恐怕都是难以度过的。
革命是熔炉,从这里面淬炼出来的人,又怎么可能是凡人。
而设想一下,当周恩来见到邓颖超历尽生死来到他身边,对这样的妻子,又怎么可能不敬不爱呢?
03
在此后的许多年里,邓随周辗转南北,也助他周旋四处、联络各方。
我看过一个比喻:说周邓不是一朵花,是两朵花。可是,如果这两朵花同时争奇斗艳,那会抢走其他太多花的光彩。
所以,就只好委屈邓大姐这朵花了。
尤其1949年以后,周总理对邓大姐的“压制”可谓是全方位的。这种“压制”在旁人,都有点看不过去。
在第一届政府组成之时,周恩来可谓事无巨细、考虑周详,能安排的都给安排了。比如,傅作义将军本已做中央人民政府委员,但周恩来认为傅将军接受和平改编、保住古都北京的功劳很大,应再安排实职。于是,就提议傅作义为首任水利部部长。
但他就是没有安排邓颖超。
这时,一位前国民党人士出来说话了。这个人不是别人,正是当年在周邓婚礼上“起哄”的张治中先生。他直言不讳地说,说什么也得给邓颖超同志安排一个部长职位,才让人心悦诚服。
周恩来听了之后笑着说:
文白先生,这是我们共产党的事,您就不必多操心了吧。
压职位也就算了,可到了工资上,还是要压。
邓颖超是1925年3月入团、5月转党的老革命,出席过“六大”、负责过机要、参加过长征。到了定工资时,邓大姐很有分寸地,只给自己定了普通部长的五级。可到了周总理那里,又给硬降了一级。
到了70年代,有人提议邓大姐出任国家领导人,可还是被周总理压下来。邓大姐甚至都不知道这个动议,还是小平同志对她说:
就是你那位老兄反对。

1970年代,邓大姐与邓公在开会。
邓大姐心里有没有委屈呢?也有。后来她在同晚辈谈话时说:
我做了名夫之妻,你们伯伯一直是压我的。
有一句话说的是:婚姻是一种妥协的艺术,是一对一的民主,一加一的自由。
那么,既是民主就有规则,既是自由就有约束,既然是妥协就不会是各让50%。总会有人让得更多一点。
04
邓大姐的隐忍,不光是作为一个懂事的妻子的隐忍,而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的隐忍。
这种隐忍,越是在复杂的环境里,越关键。这就要说到“文革”十年。
众所周知,在那十年间,周总理始终处在风暴的中心,如邓大姐所说“不过未打倒就是了”,许多与总理有关系的人都挨了整。
那十年,邓大姐给自己实行了“三不政策”:不见人、不通信、不写材料。这个“三不政策”执行之彻底,就连亲属也不例外。
不见,是为了保护她们。
所以,翻看邓颖超的生平资料,“文革”中她除了关照总理的身体,就几乎找不出来什么别的事。

周邓晚年在西花厅。
但即便在隐忍之中,邓大姐也不是没脾气,而是有脾气的。
据秘书赵炜的回忆,曾亲眼见到过“大姐和总理”动气。那是在1973年冬天,她正要去找邓大姐,却看见周总理神情严肃地往外走,“一眼就能感觉出他心中有股尽量压抑住的气恼”。
见到秘书来了,总理只说了一句话:
赵炜,你在这陪陪大姐,安慰她一下。
秘书走进房间,只见大姐手扶着椅子呆呆地站着,“也是一副十分生气的样子”。秘书并不敢问缘由,只是悄悄地走近她身边。
那么,他们会因为什么事动气呢?
我试图找出一些旁证,但没有成功。不过,引人注意的是这个事发生的时间点:1973年冬天。
据《周恩来年谱》记载,在那年11月至12月间,周总理因外交上的一些事情,被污蔑为“投降主义”,遭到错误批判。总理的卫士高振普同志,曾回忆过这一段,当时总理已身患癌症,可批判他的会还是开了十几天。
周邓是不是因为这件事,产生了不同意见呢?
就都不知道。
05
我觉得邓大姐与总理相伴,是不容易的。
不容易的地方就在于,她一边作为妻子,应当享有妻子的权利;一边作为党员,又必须要严守纪律。一边作为独立女性,应当有自己的天地;一边作为“名夫之妻”,又不得不做出牺牲。
这种矛盾,即便在总理故去之后,依然在她身上体现着。她时常追忆与总理的往事,也偶尔发些“牢骚”。
比如,周邓都不直接管钱。总理曾当着大姐的面问卫士,“我现在有多少钱”。注意,他说的是“我”,而不是“我们”。邓大姐在一旁听着,就不高兴。
晚年时,她提起这一桩事就抱怨说,“他脑子里没有我,大男子主义”。
这个阶段,邓大姐需要顾及的东西少了,说话做事更为直接,更像年轻时的演讲队长。
1982年,国家决定编辑出版《周恩来传》。按说出版自己丈夫的传记,是件很好的事。
可是,当文献研究室的同志来到西花厅听她意见时,邓大姐的态度似乎没那么“积极”,她说:
我要重申一下,对恩来的事,关于他的东西,我不直接提意见。不过,你们来找我,我不是完全不负责任,如果你们需要核对一些事实,我不推卸责任。
这些话,让邓大姐的形象,变得更为生动而立体。
所以,像所有的爱情一样,周邓之间也并非只有情话。这些来自女方的“牢骚”和“抱怨”,也能反映他们感情生活的真实面。
在某种程度上来说,是周选择了邓,也是邓成就了周。
也是在那次同《周传》写作组的谈话中,邓颖超说了一句话,我觉得道出了她的心声:
希望你们不要把我,当做周恩来一辈子事情的一部电影。不要以为我什么事情都知道。
秦安配资-配资实力股票配资平台-现在还有实盘配资吗-配资平台股票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